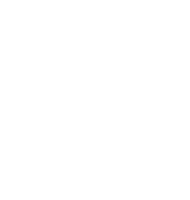新闻资讯
注重“学识之创获,品性之陶熔,情怀之沉淀”
画社资讯
坐拥太多艺术品的新富阶层,幸福吗?
|
|
|
2014年11月,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以约合3.7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得梵高油画《雏菊和罂粟花》。 2015年11月9日,刘益谦以约合人民币10.84亿元买下莫迪里阿尼作品《侧卧的裸女》。 近十年,我跟新富们多有接触,由于性格及众多因素,他们在当代艺术圈的人生亦像一出“浮生记”。我1998年到北京,2000年在成都的上河美术馆策划了“转世时代”展览。馆主是出身于建筑师的地产商陈家刚,他将售楼处改成美术馆,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末国内三大民营美术馆之一。那时所有艺术大腕都围着他吃饭,我还曾旁听他与潘石屹高论如何统一地产江湖。但数年后,项目破产,那些围着他的人也不见了。他倒洒脱,拿起照相机做起了艺术家。 2003年我在炎黄艺术馆的环碧堂画廊策划了“青春残酷”展览,画廊主是李国盛,工人出身,从1990年代初倒邮票开始,然后炒股票、期货、明清家具、古玩、地产,完成了资本积累。老李后来对艺术圈逐渐了解,有次跟我聊天,说批评家收入太少了,与所作贡献不对称。在市场火爆期,他抱怨一些70后画家不讲情义,落魄时要求画廊包销作品,等做出了市场,又要单飞。过了几年,听说老李在澳门赌博输了很多钱,抛掉了不少手中的作品。后来,有一次在华威桥的古玩城旁碰到他,老李说不做画廊了,准备干老本行古玩。老李其实不太懂艺术,他一生都在倒货。 这些年打交道下来,发现新富阶层并无幸福感。在完成了财富及消费体验后,他们找不到终极归属感。不能在社会上自成一体,想成为某一领域的专业领袖,但在财富上和知识上都达不到,因此,他们有一种不上不下的虚无感。他们中的一些人喜爱文化或艺术,但骨子里仍是商人。因为在自己的圈子里做惯了老板,所以他们没有艺术圈的那种平等意识。比如参加饭局,有些人尽管面子上跟艺术中人混,但看得出来不爽。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有人奉承,一旦在饭局上不以他为中心敬其三分,他们会很难受。 不少新富商经过长期的商战训练,已设计出一套模式,保证他们能将任何事情纳入其商业,并保证不吃亏。要他们哪怕赞助学术几千元都不愿意。比如据圈内人士透露,上海某知名民营美术馆馆长出手购买艺术品可以花几个亿,但请专家讲座却为几百元钱讲座费讨价还价不休,真真让人匪夷所思,想想也正常——学术中人如果对这些暴发户们心存幻想,只会浪费自己的精力。这些暴发户们即便拥有太多的“艺术品”,但很难说他们是什么收藏家!他们幸福吗?其实有时觉得,他们在精神上是很可怜的一群人。 |